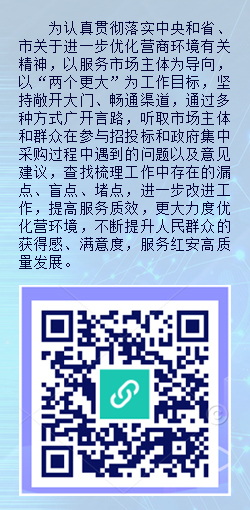|
造城运动如火如荼
国际化都市是所有城市建设的终极目标吗?作者以古老的北京城为例,痛心疾首于当前大规模的旧城换新城运动。城市由人而生,为人而建,然而在如火如荼的造城运动中,普通城市居民的利益被损害,最可怕的是,原有的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也会遭到致命破坏。
居民流离 古宅伤逝
我生命中的北京,由纵横交错的胡同织成。那些细细弯弯的胡同如同纤巧的神经,贯通着京城文化的底蕴。浓浓树荫下延绵的灰墙,是通向心灵的小巢。我常穿着拖鞋踱到胡同口的小铺买切面,倚着刻满岁月纹路的木门儿与街坊聊天。胡同尽头的小街窄窄的,通着一趟慢悠悠的公交车。
可惜,如今在推土机下快速消逝的胡同,正在扫荡心灵的家。
前几日去北京花市地区一家大型商城购物,大白天的冷冷清清,因为商城对面大片的胡同区已拆成一片碎石烂瓦,在此地居住了几代的市民被“疏散”到了城市边缘。站在气势恢宏的商场门前,遥望马路对面凄凉的废墟,不觉怅然若失。那些镶嵌在青苔中凸凹不平的石板路呢?那些荫蔽一代代家族的参天古树呢?那些掩映在海棠树下的胖大鱼缸呢?那些佝偻着腰转出影壁的老人呢?那些世代为邻的街坊呢?全成了永远的回忆。胡同没了,城市中心的人气也就散了。
花市那些明清时代的老宅子“死”得真惨,无论是院主的苦苦抗争,还是文物保护单位的紧急呼吁,都没能挽回它们灰飞烟灭的命运。它们逃过了战争,逃过了文革,却没能逃过现代城市改造的狂热。手快的房主从“虎口”中夺下一扇雕花格栅或是一对精美的门礅,留做伤逝的纪念。胡同文化是多么顽强,穿越几百年而不衰;又是多么脆弱,经不起一张拆迁告示。
“包装”变味特色枯萎
颇有讽刺意味的是,当有关部门把平民四合院当垃圾扫荡之时,外国人却依然青睐四合院。于是那些在拆迁中“合法”转移产权的四合院修缮后被卖出了天价。据说,北京保存完好的四合院仅剩三千多个。虽然资源稀少但销售并不看好,因为看到前房主的命运,新买主没有安全感。况且,那些“包装”后变味儿的新四合院也难成为北京文化的代表。仅以皇城范围内停止成片拆迁,更不足以保存北京特色。被林立高楼围起来的皇城,将成为枯萎的标本。
城市特色需要“活”的建筑来支撑。它活在胡同中疯跑长大的孩子中,活在大树下安然下棋的老人中,活在市井小民的家长里短中,活在大杂院此起彼伏的京腔中,活在承载数代家族记忆的老屋中,活在私有房产的安全中。单为参观与旅游者而规划的城市,未免矫情而浅薄。
在以可怕的速度扫荡胡同之时,北京塞满了洋味儿十足的宏伟建筑。“德国原版”、“南美风情”一类的房地产广告满天飞。京郊的别墅群中,充斥着不同风格古典洋楼的复制品。CBD(中心商务区)的商圈吞噬了胡同后,为汽车而加宽的马路又抹去了无数方便人行的小街。
消灭城市个性运动由北京而蔓延全国,符号式的气派广场、有震撼力的大楼,无情地扫荡了平民朴素而安静的住宅。据统计,中国六百六十一个大中城市中,有一百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,二百多个要建CBD。许多城市甚至是“一届政府,一届规划”。
畸形建筑充斥城市
“征服”城市的“豪迈”运动,让有良知的专家心痛。
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说:“在国外往往只是书本、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,现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数大城市真正地开始盖起来了。畸形建筑结构动辄花费十亿、十几亿、几十亿,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?”
曾多年参与北京城市建设的美国城市规划专家苏解放说:“北京这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,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。为什么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,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,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?”
哈佛大学归国的著名景观设计师俞孔坚说:“我跑过中国上百个城市,到处看到对海岸的破坏,对土地和河流的破坏,对森林和草场的破坏,我看到太多的城市在建造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,建造无病呻吟的广场,看到我们的城市到处充斥着令洋人倾倒的景观,奢华的、封建的、帝王时代的建筑物充满的公共空间。”俞孔坚认为,一个国家越发达、越文明,它越知道平常的重要性。城市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平民文化———普通人的文化。
百姓住进“小盒子”
对普通百姓来说,容忍其安全留在旧房子里,往往比迫使他们在弱势条件下搬迁更为人道。
大拆大建后的城市不一定会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,反而往往产生新的贫民窟。我曾到过一座回迁平民住宅楼,那里拥挤黑暗,白天也得点灯。许多老人被困在楼上盒子般的小屋中,半年也下不了一次楼。幸运地被“改造”后的胡同更好吗?看看南池子吧,那里规划整齐得如一个供人参观的电影城。低矮的“四合楼”极不舒适,上层竟然没有厕所。在疯狂的拆旧建新中,买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,一辈子吃苦为房打工成为不少人可悲的命运。有市民说:居不能宜,还谈什么宜居?
面对改造后华丽气派的城市,我们在赞叹之余是否有权追问:造城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是谁?有没有人因此而被“扫”到城市边缘?有没有人因断了生路而陷入赤贫?有没有人背上沉重债务?有没有人的私有房被巧取豪夺?有没有人因此踏上茫茫维权之路?
修旧复新为民兴利
当我们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看齐时,人家早摒弃了浪费能源的造城运动。欧洲城市几乎看不到大拆大建,能看到的是对古代建筑持续的修缮。英国不少百年以上的楼房,都保养得好好的住着市民。修旧复新建筑方式在欧洲蔚然成风。在挪威首都奥斯陆,一栋一九五三年建成的大桶仓废弃后,政府对其再利用进行招标,中标用途是改建为大学生公寓。改造后不仅功能上佳、造型独特,而且保留了粮库文化的象征——电力机车车头和粮秤,这和我国目前对待老建筑一拆了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在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中,我国建筑平均使用寿命不到三十年,而欧洲建筑平均寿命周期超过八十年。我国建筑能耗吞噬了社会总能耗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城市形象为何一定要以标志性的建筑来展示?民族特色与环境美好才是衡量城市形象最重要的标准。许多发达国家就用环境美好来展示城市形象。比如美国华盛顿的城市形象就定义为“树木之城”。华盛顿市区的林木覆盖率为百分之二十八点六,居民经常在树下休憩、野餐。树林除了带来阴凉外,在净化空气的功能上每年还可为市政减少数百万美元的开支。
城市是否人性化与体制息息相关。优质的城市规划需要制衡机制下的公正程序,这种程序才能反映全社会共享的价值观,才不会把城市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城市建设的决策取向之外。中国城市已经意识到毁灭个性的危害,例如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,决不刻意为世博会造任何标志性建筑。
造城运动如火如荼之时,应该冷静地问一声:城市为谁而建?或许不远的将来,疯狂的造城运动不再成为官员上升的阶梯;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,才是检验城市价值的唯一标准。
|